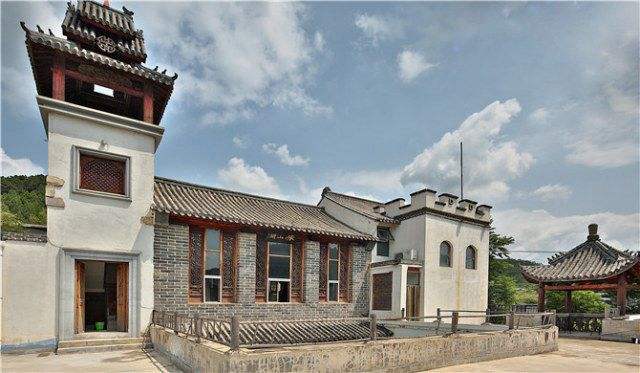云岩昙晟禅师的禅法讲述
发布时间:2020-06-23 17:03:32作者:正觉网整理云岩昙晟禅师所保存下来的机缘语录并不多,在《祖堂集》中,著重的记载了他开示洞山良价的语录,而在《景德录》中,所记其机缘语录也甚少。但我们透过这些有限的的机缘语录,至少可以窥见出他上承石头衣钵,下开曹洞宗风的历史原貌来,因此,我们很有必要将云岩昙晟禅师禅法的主要特色,作一些粗浅的阐述。

云岩亲炙百丈达二十年之久,他对于百丈那种身体力行的农禅精神,显然是有所继承的,我们从昙晟的行状中所发现他亲自锄姜、煎茶、作鞋、扫地等作务,就可以见出其一斑。也许因为他学习了百丈的那种踏实肯干的作风,因而在云岩山那种比较艰苦的修行环境里,仍然能使宗风大振,最终完成好了药山的传灯慧业。但昙晟在对禅法的体认上,却是直承药山的,他对于禅的本体作了深浚的体证。在《祖堂集》卷五的昙晟本传中,有人举石头希迁回答学人“如何是祖师意”时所说的“老僧面前一踏草,三十年来不曾锄”去请益昙晟,昙晟说:“牛不吃栏边草”。[六]其实,这牛之所以不吃人送到牛栏边的草的那一开示,非但告诫了学人“从门入者,不是家珍”的禅理,同时也暗示了昙晟对希迁当年禅机的遥相心印。至于昙晟对药山那“石上栽华”式禅机的体悟,则更是直接承嗣了。在《景德录》中,载药山问昙晟曾去过广南否后,便向他询问起“弄师子”一事来了。药山问昙晟弄得几处,云岩答“弄得六出”;但药山进一步开示他说“我弄得一出”,昙晟此时立即回答药山:“一即六,六即一。”[七]在这里,药山他们师徒所说的“弄师子”并非只是民间的那种游戏,而是暗喻了敷扬佛法这一大事因缘[八],至于他们师徒之间的弄得六出或弄得一出可以姑且不论,单凭弄得师子,就足以大弘法教了。不过,昙晟这里的“一即六,六即一”的回答,不只是包含了始自石头的体用圆融的禅旨[九],同时也意味著他堪为药山的法子,完全可以肩负起弘传石头禅法的重任。值得注意的是昙晟的“一即六,六即一”的禅机语,发展到了洞山那里则成为了“五位”禅法,其中的“重《离》六爻,偏正回互”之禅法应当源始于此无疑。但在石头的门下的天皇那一系禅中,法眼文益的“华严六相义”,至少是从这里得到了某些启示吧,否则他们之间何以会如此地不谋而合呢!显然,昙晟在发扬百丈农禅精神的前提下,他所承嗣的禅法全部是药山的,像上面这些禅机无疑也足以体现出这种特色了。
昙晟对药山道统的承嗣还体现在其他方面,比如他的禅教一如乃师、乃祖那般霭如平和,而又寄寓了深邃的禅理,这些只有在药山门下才可以体得。例如,《景德录》载有学人问昙晟“从上诸圣什么处去”,而昙晟没有直接回答,他沉吟良久后反问那学人“作什么”。在这里,昙晟的不立即回答,分明是要使那位学人休歇驰心,而等到他那驰心稍微休歇之后,昙晟又反把他提撕起来,使之自悟。又如有学人问昙晟“暂时不在,如同死人如何”,昙晟则如利刃斩葛藤一般说:“好埋却!”在这里,昙晟的接机却又不乏剀切的顿教之风。如此高邈的禅境,绝非一般禅和的见地,我们从这里可以真正发现昙晟与药山的禅法师承之间,就如同“一机之绢”,彼此水乳交融。
昙晟的禅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禅教实践之中,在昙晟的云岩道场,即使是日常的作务,也可以给门人提供开悟印心的因缘。例如,昙晟有一次在煎茶,其师兄道吾问他煎给谁吃,昙晟说“有一人要。”道吾则问他“何不教伊自煎”,昙晟说:“幸有某甲在。”[一○]道吾与昙晟虽然是师兄弟,但在面对禅机勘辩时,何况是师兄弟,就是师傅也无须迁就(在丛林中素有“临机不让师”的说法)。在这里,不管道吾如何来扣问,昙晟始终都没有说穿那个“人”。事实上,五蕴和合的那个“吃茶人”,与脱离了诸漏的“自在人”之间,完全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,因此,若道著实存的“五蕴人”即会违背佛法,若道著那个“自在人”却又违顺世情,所以还是昙晟的“有一人要”说得最妙。又如:

师扫地次,沩山云:“太驱驱生!”师云:“须知有不驱驱者。”沩云:“恁么即有第二月也?”师竖起扫帚,云:“是第几月?”师(当作“沩山”)低头而去。
在《祖堂集》中,上文里的“沩山”作“寺主”。也许昙晟在离开药山之后还去过沩山,然后才住持云岩的,因此后来沩山才有可能指引洞山到云岩那里去参学。在这里,我们姑且不去论是“寺主”还是“沩山”,当昙晟在从事扫地劳动时,人家说他“太驱驱生”,而昙晟同样也是用“须知有不驱驱者”(即有一个“不驱驱者”存在)的,至于那个“不驱驱者”,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当对方问到“恁么即有第二月也”时,这也显然是一种反常的机锋语,因为世间的一切法(事物)都是虚妄不实的,这也如有目疾者看到了第二个月亮一样(在《唯识论》卷一中称为“毛月”)。而站在了义佛法的实相第一义谛上讲,则不可能有一、二之别,这也就如同《法华经》中佛广说三乘,而最终唯有一佛乘一样。面对这“第二月”之问,昙晟只是竖起扫帚问对方是“第几月”,实质上也将那离言绝相的第一义谛给指示出来了,以故沩山低首(《祖堂集》作“寺主无对”)。
还有一则公案,足以见出云岩对药山的承嗣,同时也可以从中见出他对洞山“偏正回互”思想的直接影响。《景德录》卷十四本传载:
师问僧:“什么处来?”僧曰:“添香来。”师曰;“见佛否?”曰:“见。”师曰:“什么处见?”曰:“下界见。”师曰:“古佛!古佛!”
面对那位添香的僧人,昙晟却去问他见到佛没有,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有一点明知故问了,因为香炉旁边就是佛像了。那么。昙晟何以要这样去问呢?实质上昙晟的所问中还包含了另外一重含义:即是否见到了佛的偶像之外的那个真容;抑或更深一层次地说,是否见地到了本来清净的自性佛。那位僧人也颇为伶俐,他回答昙晟见到了;当昙晟进一步问他在何处见的时,他却说是在“下界见到的”。按照常理来说,佛不只是超越了六凡界(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、天)的地位,而且还居四圣界(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)之首位,这是断然不可能会处下界的;但如果站在佛法周遍于十方一切界的见地上来讲,何处又没有佛呢?因而昙晟对他连声以“古佛”印可。在昙晟看来,佛法是周遍一切法界的,同时也是不受时空条件所局限的,因而在回答道吾来问他“初祖未来此土时,还有祖意不”时,云岩非常肯定地回答:“有!”当道吾再度反问他“既有,更用来作什摩”时,云岩说:“只为有,所以来。”这个“只为有,所以来”,也就正好可以当作上面那则公案的注脚,它说明了达摩之所以到中土来,也就因为这里的人有证悟大乘佛法的觉性。
从昙晟的煎茶、扫地、与他勘问学人的添香等机缘语中,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在吸收百丈的农禅作风,而另一方面在禅法上则承嗣了石头这一系体用圆融的禅学思想。即便是煎茶中的“有一人”与扫地中的那个不“驱驱者”等机辩,也无不是从日常的细行中以见出禅法的本体来,至于他去勘问那个添香的僧人,也无非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机辩例子了。可见,在禅法的承嗣上,昙晟是直承药山的,他那“一即六,六即一”的机辩,何尝不是药山门下那种体用圆融禅法的完美体现呢?但对于昙晟来说,他的最可贵之处,还在于他那种踏实肯干的禅行,也是因为他具体了这样一种精神,因而他也具体了办道的能力,也堪为承嗣药山法脉的门人。记得昙晟有一次问学人“世间什摩物最苦”,学人回答“地域最苦”,此时昙晟告诉他:“地狱未是苦,今时作这个相貌中,失却人身最苦,无苦过于此苦。”因此,昙晟时常告诫学人努力修行,只有“向这个相貌中失却人身最苦,无苦于此苦”。

上面就是关于云岩昙晟禅师的禅法讲述,师兄看了之后,肯定有了一番自己的感悟,而且多了解这些知识,对学佛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。